孙英春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教授。 孙英春教授被确诊为“新冠肺炎”重症后,在医院待了28天。从一度危重,直到最后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,他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:用手机拍下了大量第一视角的照片。他拍下ICU窗户上看雪的护士、病房窗户外的阳光,那些照片,仿佛总是有“人性”的微光在寂静的海水深处悠悠显现。当一个人几乎被死神征服的时候,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拍下这六百张照片的呢? 1 他一直坚持做的事:记录 北京市第35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是孙英春。 他是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知名教授,大半辈子都在想“如何做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”,但是这个愿望在1月24日确诊为“新冠肺炎”重症的时候,差点咔嗒一下中断了。 “愤怒”、“恐惧”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思想。他在医院待了28天,从一度危重,痛苦得“宁可砍掉双臂换来一口呼吸”,直到最后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,转入普通病房,他一直在坚持做一件事:记录。 他用手机拍下了大量第一视角的照片,一是作为老媒体人的本能,二是他担心万一有个三长两短,自己还能留下生命的痕迹。 而我是在朋友的朋友圈里读到了他的故事,我想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和他聊聊,当一个人几乎被死神征服的时候,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拍下这六百张照片的? ▲1月12日傍晚,孙英春在武汉长江大桥上,用手机拍摄的照片——当时,看这暮气里的城市,有一种莫名的氛围,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感。因为在那个时候,他已经知道武汉有了疫情,但万万没想到,疫情会发展到后来的地步。 2 “凭什么让我遭遇这种无妄之灾” 孙英春是1月24日确诊的。他回忆说,只有一个可能性,那就是1月14日坐高铁从武汉回北京的时候,在车上,因为要吃东西、喝水,不得不取下口罩。 在此之前,他1月9日回武汉探望父母,基于之前的人生经验和看到的外媒报道,他全程都很警惕,几乎没出过门,还给父母买了几百个口罩。固执的父亲不相信疫情如此严重,“刚刚看过,新闻里说是不会人传人”。 这怪不得父亲。直到孙英春因为身体无力,发烧了去地坛医院检查,给他做检查的第一个医生杨松也不相信。 “他虽然已有七八成认为我是疑似,但还是不愿意相信。他先是拿了血氧仪重新给我量血氧,因为血氧是个特别重要的指标。他一量,不高,但他不相信,然后他接着量其他几个指头——我看到了一个好医生那种发自心底的善良,不愿意你是这个病……” 孙英春用手机拍下的第一张照片,就是杨大夫给他量血氧,他被确定为高度疑似,然后去做CT,结果出来之后,杨大夫说你准备住院吧,我基本上判断你就是了。 ▲1月23日亲手测量血氧的发热门诊杨松大夫。 主管医生宋美华当机立断,采取了一个针对确诊病人的治疗措施——后来孙英春最庆幸的就是这件事,他认为大部分的医生都未必能做到,因为要等核酸检验的结果,至少得24小时,但是这么等着的话,会耽误治疗。“所以她就跟我商量,说我认为你已经高度疑似了,我要给你马上用药,就把你当成确诊的病人治疗,你同意吗?这个几乎是很救命的一件事情,我就同意了,然后马上就给我用药,24小时之后,病情还在发展,就直接把我送进了ICU病房。” ▲出院时孙英春与宋美华医生合影。 确诊之后直到现在,他都非常愤怒:“我在武汉一直劝说父母要戴口罩,父母说武汉人没有这个习惯,但在我的坚持下,还是答应了。而他们在1月14号下午去同济医院体检,还打电话跟说我,医院里看病的没见到戴口罩的!”多年来他一直有戴口罩的习惯,坐地铁,去公共场所,这次去武汉也是,自己防范意识那么强,却还是中了招,他想不明白:“凭什么我要遭受这种无妄之灾?” 3 隔壁的病人已经崩溃了 通话时,孙英春还在出院后的观察、隔离阶段,我无法通过电话猜测他的表情,但在他讲述自己经历的一个半小时中,即便提到“愤怒”这样的词汇,音量也没有提升。他逻辑清晰、思维敏捷,甚至有的时候会让人恍惚——电话那头,是一个在学校大课堂里侃侃而谈的教授,而不是一个在追忆九死一生经历的康复病人。 但在他那些尽可能理性的描述中,我还是对于那个叫做“ICU”的病房充满了恐怖的想象。 他说那是一个像太空舱一样的地方,里面摆满了仪器,医生护士穿着“太空服”走来走去,有一种不知道是什么功能的换气机器一直在吹着嗖嗖嗖的冷风。刚进去的时候,一整排的医生就在那讲着自己的各种生理指标,病人不是“不明觉厉”,而是“不明觉惧”——指标似乎非常可怕,孙英春不是很懂,但医生们那种表情,那种态度,不可能不让人紧张害怕。他看过电视剧《大宅门》,记得白三爷的一句台词:我他妈我了(完蛋了)——他说,当时脑子里有一瞬间的空白,然后出现的就是这几个字:我他妈我了。 ▲入院第八天,孙英春能站起来后拍摄的ICU病房。 他还对我说:“当时要是能用手机拍下这个情景就好了,因为担心ICU不让用手机,我不敢拿出来,这真是非常遗憾,当时要是把这一圈都拍下来,那太牛了。” ▲在ICU每天要吃的药物之一 。 但他很快就没能力注意这些了,接下来的几天,他身体状况在持续变糟。孙英春身高192厘米,体重200多斤,他还有高血压、脑脊髓炎等基础病史,前一年刚住过院。他是一个同学群的群主,里面是十几个关系最好的本科同窗,这些同学每天照旧东拉西扯、嬉笑怒骂,白天的时候群里热闹,他也很享受这些,有时会忘掉自己身在何处,但是到了深夜,当他面对自己一个人,最痛苦的时候就来了。 “我告诉你准确的描述是什么?呼吸到最难的时候,你宁愿砍掉自己的双臂,我不要双臂了,都不要了。只求你给我留一口呼吸,就让我能够正常呼吸……”在ICU的前一周时间里,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,还是感觉晕过去了那种短暂的睡法。 孙英春说,人在这种极限环境,就会发现宗教信仰能帮上忙。他一直对佛教有比较特殊的亲近感,他曾经去尼泊尔探访过蓝毗尼,那里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出生地,庭院里有一株古老的菩提树。当无边的黑暗和未知的恐惧袭来,“我会想象自己在菩提树下行走,一步步地,一圈一圈地……” ▲孙英春在蓝毗尼的菩提树下 2019年8月。 到第七天的时候,孙英春觉得自己的精神可能要出现问题。他能听到,隔壁病房的一个中年女性常常会大呼小叫,护士解释说,这个病人的生理指标改善了,但精神上出了问题,总想着出去。他认为,这可能是因为在ICU看不到外面,产生的幽闭感所导致的,他自己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——病房里有一个小窗户,外面是过道,再就是看不到任何东西的“白墙”。 但就在那一天,孙英春发现,那不是一面“白墙”,而是一道窗帘——是过道里的白窗帘放下来了。这个发现让他特别激动,“我就让护士帮忙把窗帘拉上去,但偏偏这个窗帘坏了,护士拉不上去就放弃了。但是我当时确实是忍耐不了,就是把我自己身上各种线各种设备拽下来,我也要去把窗帘拉上去!” ▲幽闭的ICU病房,只能从这个小窗看到外面的通道。 后来又来了一个医生,孙英春又坚持跟医生沟通了这个想法:“请您无论如何都要帮帮我”,“医生听了我的意见,转身就出去摆弄那个窗帘了”。 这位医生叫刘景院,是ICU病房的主任,个子并不高,比孙英春还要大一两岁。孙英春从门缝看到,刘医生踮着脚弄了很长时间,最后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把窗帘卷起来,还捆上了。 当时孙英春就感觉特别放松,终于透了口气了。 ▲主任医师刘景院(右二白色防护服)等来病房。 两天之后,孙英春出去做CT,他在门口看到窗上还有一张纸条——刘景院医生卷起窗帘以后,在那个窗户上留下了一个纸条:“窗帘不要拉下来,孙教授要看风景。” ▲孙英春当时看到这个纸条,不是感动,是一种震撼。 4 刮胡子也是抗争 孙英春的人生经历很丰富,他在中央电视台做过电视编导,在人民出版社做过图书编辑,非典的时候,在大陆和台湾同时出版了一本公益书《非典时期心情处方》,帮助大家如何进行心理自救,“对于心理援助这些知识,我不比很多专业人员懂得少”,作一个内心坚定的人,他要进行抗争、自救。 ▲2003年,孙英春编著的《非典时期心情处方》,在大陆(中国旅游出版社)和台湾(远流出版公司)出版,稿费全捐。 诊疗之外的时间,他一刻都没有闲下来过,甚至尝试过,让好友弹奏不同的古琴曲,测试血氧的变化,“有的音乐听完,血氧值测出来就会偏高,有的音乐则会偏低,最好的曲子是《鬲溪梅令》”。 到第八天,他感觉自己的病情开始走出低谷,就开始反复听一段音乐,那是电视剧《我的团长我的团》里一段白刃战用过的音乐《战场》(Battlelines)。 他在自己的ICU笔记这样写到:“那段白刃战的视频我看过几遍,记忆非常清晰,听这段音乐,也让我血脉贲张,我要呼唤我的免疫力、我所有的力量、亲人、战友、朋友,跟病毒决战,我不怕你!” 除了呼吸困难,最痛苦的是大小便,因为需要有护士来帮忙,这是最难堪,也最难过的。 尤其好多护士是年轻的女孩子,怎么好意思让她们帮忙?有时候就忍着,等看起来岁数大一点的护士来了,自己才张口。“在ICU那样的地方,人的尊严都没了”——而这也是孙英春同意我把他的故事写下来的原因,“都经历过那样没遮拦的时候了,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”。 ▲ICU的护士们。 ▲从肝炎病房支援的小护士,跟孙英春说自己胆子小,晚上下班不敢回家,就住在值班宿舍。 ▲北京小妞 护士长王颖。 因为使用吸氧管——插在鼻子上一种粗大的管子,胡子长长了,就影响到了吸氧管的位置,很扎很难受,“护士太辛苦太忙了”,当身体能动弹一些的时候,他决定自己刮。 虽然带来了剃须刀,但是没有剃须膏、肥皂,病房没有这些东西,外面又送不进来。他上网检索攻略,发现有人用牙膏代替,他就试了,但在床上清理剃须刀很麻烦:只能用非常少的水,废水用塑料袋盛着。他用了将近两个小时,刮了上嘴唇,留着下嘴唇没刮,看上去有些奇怪。 ▲准备用剃须刀加牙膏刮胡子。 ▲刮了上嘴唇的胡子之后。 他还坚持每天清理鼻腔、口腔,清理肺里面的痰液。清理鼻腔,是因为24小时插着吸氧管,如果鼻腔里面如果不干净,吸氧的效果和身体感受都会有很大影响。他需要拿纸巾蘸水,然后把每个鼻孔最深处一点一点清理干净。清理工作最大的难度,是需要同时吸氧,如果不吸氧,血氧值会迅速降低,房间里的检测设备也会立即报警。他就试着用嘴含着吸氧管,然后清理鼻腔。这也是一种很糟糕的体验,“我那时候用的氧气量已经差不多是供氧设备允许的最大量了,是什么感觉呢?就像有人拿最大号的打气筒往嘴里打气,正常人含在嘴里,根本就顶不住那个气。其实你嘴都含不住,得用牙咬着。” 刮胡子,清理鼻腔,每天三次刷牙,用湿纸巾擦全身,按摩肢体,收拾小桌上的杂物,每天24小时的大部分时间,他一直在一点一点地完成这些动作,同时尽量保持血氧、心率和血压的稳定,因为如果这些数值发生显著的变化,医护人员随时会阻止他做任何事。 这些事情,不仅仅是一种仪式感,这是对自己生存意志的考验,点点滴滴,都是在唤醒自己跟病魔抗争。 ▲春节期间物资送不进来,护士刘杨带给孙英春的湿纸巾,要不就没得用了。 5 “李文亮在这的话,能治好吗?” 孙英春缓过来没两天,病情又有反复,那天李文亮医生走了。 看到李文亮医生去世消息的那一夜,是孙英春在ICU期间最难熬的十几个小时,他一直在流泪,控制不住。第二天早晨,医生发现血氧下降了,有些生气,“他看我眼睛都是红的,就说你怎么搞的。我就跟医生说,是因为李文亮”。医生也叹气。 孙英春说,他知道负面情绪会对自己的病情有影响,但当时的那种情绪,是完全控制不了的。 “我相信,那夜为李文亮哭泣的所有人都是一样,不光为了李文亮,也是为了自己,为了这个社会。” 孙英春有个一百多成员的学生群,就在李文亮离开的2月7日,他第一次跟学生们公开了自己在ICU的事情,“我说今天我不是告诉你们我在医院,我是想希望大家能记住今天,有一个叫李文亮的医生走了,我是希望你们能记住他。” 有学生也问他,“老师我们都很迷茫,我们该怎么办?”他在群里写了一段话:“我希望你们在学校的时候,能读真正有用的书,做真正有用的思考,写真正有用的论文,将来工作了,做真正有用的事。” 那一天,孙英春问了几位医生和护士,“如果李文亮在咱们这里,能不能救活?”每个人都告诉他:“能,一定能”。 ▲进ICU十天左右 第一次站起来的自拍。 6 日出和日落 在ICU住了14天,在普通病房又住了14天。差不多一个月的隔离生活,漫长得就像半辈子。有一天他偶然浏览自己的微博,看到了一个人问候的私信,那是他在1月9日去武汉高铁上遇到的一对广东汕头夫妇,他们在北京做点生意,这次是去漯河探亲,路上一度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一位抱孩子的年轻妈妈,临下车时,还托孙英春帮这个年轻妈妈从行李架拿行李。后来,孙英春不光帮她拿了行李,还帮着送到了出站口。 这对汕头夫妇在电视上看到了有关孙英春生病的报道,认出了他,就让女儿根据姓名搜索,终于通过微博送出了问候。 看到这个问候,孙英春感到“心里暖”,他在自己的同学群说起了这件事,他还跟自己的老同学难得地说了一句“高大上”的话——“中国人之间,地不分南北,只要是好人,彼此很容易产生一种亲近感。这是我们这个文化的伟大之处。” ▲被让座的年轻母亲,在北京某医院工作的护士。 孙英春说,“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,其实是看陌生人之间的关系。”他还说起,上世纪90年代初期,他在央视做编导,曾经做过这个主题的纪录片,但播出前被要求修改,他随后就离开了央视。许多年过去,他依旧纠结于这个问题。 在病房,只要有体力,每次得到医护人员的帮助,他都会认真地说一声:“谢谢”,他也问过医生和护士,有多少病人会说“谢谢”,一些人不会回答,一些人会说:差不多一半吧。 ▲2月6日刚做完手术穿着特殊防护服的医生。 ▲隔离病房的护士。 在病房,他一直注意个人卫生,每天都会尽量把生活垃圾收拢,方便保洁员打扫,每次保洁员来清理,他同样会认真地说声“谢谢”,他也问过保洁员,有多少病人会说“谢谢”,会自己把生活垃圾收拾起来,方便打扫?一个来自内蒙通辽的大叔说:都差不多一半吧。 ▲保洁员 内蒙通辽人。 ▲能站起来使用卫生间之后,孙英春自己烧开水,用了一天时间,边歇边干,把卫生间烫了一遍。 孙英春长期关注医患关系。前些年,他曾经因为数次被医生误诊,不仅吃了毒胶囊,身体和生活也遭受了巨大的痛苦。在他2012年4月的微博里,还留着一句话:“庸医与毒胶囊双管齐下、比翼齐飞,这就是中国的现状”。在他一本学术著作的后记里,还写了这样的话:“作为人文社科工作者,倘看不到自身知识和心智的局限,不能以客观、敬畏、真诚的心态去面对学术和现实世界,其罪过于庸医!” 但在地坛医院的病房里,他也留下了许多永远不能忘记的记忆,特别是主任医师刘景院。为了给他做CT,刘医生曾和其他三个男医生一起,把他这个身高体胖的人搬上加护病床,再跟两个女护士合作,一起推着走很远的路。做一次CT,要搬起四次,一个小时以上。 ▲2月7日,从ICU到隔离病房的转运途中 。 ▲隔离病房,医护人员送老年病人去做CT 。 从1月15日发烧到23日住院,8天,从23日住院到2月20日出院,28天。在医护人员和自己的共同努力下,孙英春终于挺过来了。而我注意到他,就因为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在朋友圈发的一张老照片,和里面的一句话,这位朋友简单说了孙英春的患病经历,接着说:“有一天他在群里发了这张照片,他说:‘照片中我站的地方,已经是山顶了。从山下绕圈骑上来的。路上风景,有些像苏格兰。” ▲巴尔鲁克山,介于天山和阿勒泰山之间,“巴尔鲁克”意为“无所不有”。孙英春从小生长在新疆西部,他说,这是他小时候每天抬头可以看见的大山。在ICU和隔离病房的日子里,他常常神游自己走过的地方,特别是自己的家乡。这里是山顶的一个区域,1999年。 离开了医院,每一口呼吸都是幸福的,即使是为了防疫大计,他还要继续追加14天的隔离。好在他家的那栋楼是南北走向,东西两个方向都有窗户,无论是日出还是日落,都看得到外面的风景,天气好的时候,甚至能看到西山的细节。所以他觉得,生活还是蛮好的。 跟孙英春的短暂交流,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的知识分子,会痛诉社会的陈弊,叹息人与人之间的误解、割裂,行为上却一直在趋向善意,就如同他身处人世的深渊,也会拍下ICU窗户上看雪的护士、病房窗户外的阳光,他的那些照片,仿佛总是有“人性”的微光在寂静的海水深处悠悠显现。 ▲看雪的ICU护士。 ▲入院25天后看到的第一个日出 。 他在电话里跟我讲述这些经历的时候,不断强调自己的“幸运”,因为他进的是中国最专业的传染病医院——北京地坛医院,也遇到了最出色的医疗团队,最优秀的医护人员。因为最近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,他还说,他一直在问自己一个问题:自己的经历远没有武汉等疫区的病患和受难者那么“惨烈”,在媒体上公开,会不会挤占百姓关注的“公共资源”,甚至造成某些“误导”。 他还跟我说,他非常怀疑,这一次的经历,对他人、对社会、对未来,真有什么意义? 我跟他说:“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,他们都说,两万人死去,其实是一个人死去两万次,你的经历其实是几千几万次同样遭遇中的一个,你就是我,是我们所有人,我们都应该记录下来,不要遗忘。”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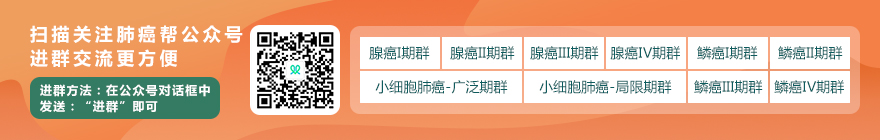

曾任美国临床肿瘤学会(ASCO)临床实践指南委员会主席
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,医学博士
Lifespan癌症研究所胸部肿瘤科主任
曾在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任职10年
曾在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癌症中心任职6年

 400-107-6696
400-107-6696



 海堰
海堰
 5640
5640
 0
0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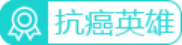
 2046
204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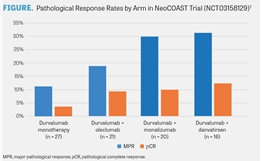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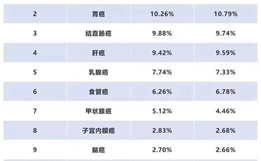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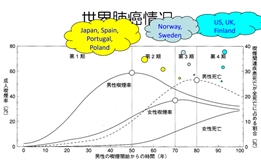
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7180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7180号
 400-107-6696
400-107-6696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