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5年8月, 91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卡特对外宣布,自己被确诊患有晚期黑色素瘤,并已做好了迎接人生“新探险”的准备。但3个月后,卡特体内的黑色素瘤却消失了。 治疗好卡特的是美国默沙东旗下的抗癌新药Keytruda,该药因此声名大噪。 药是“神药”,但价格也是“天价”。在美国使用Keytruda治疗癌症,一年的费用大约需要20万美元;在国内,一支50mg的Keytruda价格更是超过2万元人民币。 但这种昂贵,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历史了。 今年,一款被认为可媲美Keytruda的新药——PD-1单克隆抗体(以下简称:PD-1单抗)注射液已进入临床三期试验,有望2018年底或2019年初上市,而它的价格,预计只有Keytruda的十分之一左右。 带领研发这款药的,是中国人俞德超。 山里娃的大梦想 18岁以前,俞德超是街头镇一个地道的山里娃,每天除了上学就是砍柴、放牛,直到1982年,他考上了浙江林学院经济林专业,第一次走出了大山。本以为考上大学是开心的一件事,可当到了学校后他才知道,他所在的这个专业毕业后将被分配到农场种树。 “小时候天天砍树,长大了还要种树,这不是我想要的”。于是大学四年,俞德超拼命钻研学业,希望能走到更高的地方,研究期间他对“细胞结构”、“分子生物学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于是便一头扎入,如此加上他不懈的努力,1993年,这个“山里娃”成为了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后站从事药物化学专业研究的一员。 在加州大学研读博士后时,俞德超在贾滴虫中建立起基因表达系统,这一成果当时在美国学术界引起轰动,他也因此接到了哈佛大学的任教邀请。 在许多同学朋友看来,能在哈佛大学任教这是莫大的荣耀;家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:“对只知道读书、搞研究的‘书呆子’来说,还有比哈佛大学更好的地方吗?”而俞德超却拒绝了这次邀请,“我更喜欢做自己喜欢、又能帮助别人的事。”他说。 1995年完成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博士后站学业后,他先后在美国多家著名生物制药公司担任研发要职,积累了丰富的生物制药经验,成为了美国业界知名的肿瘤治疗药物研发专家。 回国创业 十年打拼,俞德超在美国的事业如火如荼,但2006年他毅然放弃美国的优越条件回到祖国,投身国内生物制药的发展大潮。 俞德超说,突破中国生物制药产业零出口是他回国创业的目标。“自主创新能力弱,产品质量、生产厂房达不到国际标准,产业化水平低、规模小,是导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落后、零出口的原因。” 回国后,俞德超作为联合创始人之一,先后创办了康弘赛金药业有限公司,成都康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,并担任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董事副总裁。2011年,俞德超离开康弘药业自立门户,在苏州创办了信达。 因为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知名度和成就,俞德超备受国内外资本巨头追捧。5年时间中,信达制药完成了4轮融资,其中D轮2.6亿美元的融资,是目前国内医药史上最高记录。 自立门户后,俞德超专注于最前沿的单克隆抗体药(简称:单抗)的研发。 在加州大学博士后站从事医药研究时,俞德超就接触到单抗的研究。单抗药物可以激活人体免疫系统,让患者依靠自身免疫力,对肿瘤细胞进行杀灭,相比化学药物其对人体的副作用极小,但研发的难度也极大。 俞德超说:“如果化学药是一辆自行车,单克隆抗体则相当于波音747飞机。” 他首先把目光瞄准了三款药:美罗华、修美乐和安维汀。这三款药,堪称当今国际上最畅销的三种生物药,其中修美乐被称为全球药王,在国内每支的价格高达7900元;美罗华对恶性淋巴瘤非常有效,在国内价格高达2万元每一支;安维汀在三者种最便宜,但也要每支5000元。 很多中国癌症患者家庭,因为无力承受这些药品的高昂价格,不得已通过各种方法,辗转到印度寻求同类型替代药(印度独特的专利法,允许印度药企仿制他国专利药品),其中的颠沛与辛酸,在网上随处可见。 俞德超带领团队,专攻这三种药的替代新药。如今,这三种新药已经全部进入到三期临床试验阶段,距离上市只有一步之遥。 偏执的追求者 信达创办之初,发生了“葛兰素史克中国行贿事件”(跨国药企葛兰素史克利用贿赂手段,谋求药品的不正当暴利,后被中国司法机关查处),国外药企普遍觉得应该在中国寻求本土合作伙伴,以共同开发市场。信达也因此进入了礼来的视野。 经过多轮谈判之后,双方都有合作的意向,但礼来提出了一个要求:信达的生产基地必须达到美国礼来的标准。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要求,但对中国药企来说,其实是一件非常苛刻的事情。 为了改造生产基地,俞德超投入了几千万美元,聘请美国医药行业最大的咨询公司PSC为信达服务。另外在信达的生产设备中,曾因为一个烟雾的走向问题,俞德超从德国搬来技术人员,大动干戈进行整改。而生产基地的评估、人员的培训,俞德超都邀请礼来的一批专家常驻信达,为此他又付费上千万。 彼时,信达研发的一种单抗药物拿到了临床批件,本来可以进入临床了,但因为没有达到礼来的标准,被俞德超搁置了18个月,失去了上市的先机。 很多人不理解俞德超的做法,在他们看来,在中国做药“上市是王,药品早一天上市,早一天赚钱”。而俞德超认为,中国生物药出口一直是零,不仅因为中国研发水平落后,产品质量不达国际标准,还因为中国的药企的厂房、管理也达不到国际标准,与礼来的合作,恰恰就是一种快速成长和学习的方式。 2015年,信达的基地最终通过了礼来的验收。当年3月、10月,礼来两次与信达签订战略合作,共获得礼来超过33亿美元的“里程碑付款”。 信达与礼来的合作,是迄今为止中国生物医药领域最大金额的国际合作,也是中国创造的新药第一次卖出了“国际价格”。 《华尔街》日报以俞德超为例,称赞中国是正崛起的生物医药大国;麦肯锡报告中说,中国2003年以来的生物制药里程碑事件,一半与俞德超有关;很多国际同行称赞信达的发展速度是可不可思议地快…… 面对赞誉,俞德超却表示,2016年全球销量前十的药物中,有8个是生物药,其中6个是抗体药,而中国销售前二十的药物中,一个生物药还没有;中国上市的96个生物药,大多是仿制药,而且仿的是美国两代以前的药,连生物类似药都算不上;中国生物制药还与国际有显著差距。 “我的理想很简单,就是想要开发出中国老百姓用得起的高质量生物药,办一家能参与国际竞争的中国创新公司。”俞德超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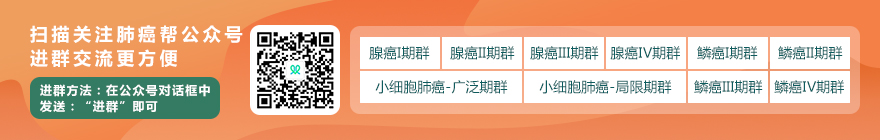

曾任美国临床肿瘤学会(ASCO)临床实践指南委员会主席
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,医学博士
Lifespan癌症研究所胸部肿瘤科主任
曾在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任职10年
曾在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癌症中心任职6年

 400-107-6696
400-107-6696



 海堰
海堰
 10552
10552
 8
8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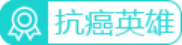
 4938
493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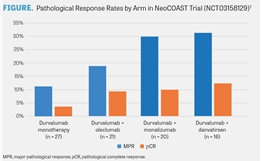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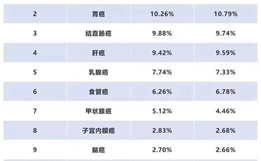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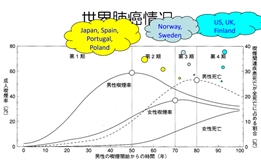
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7180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7180号
 400-107-6696
400-107-6696


